欢迎访问萧县企业家联合会官方网站!


“马虎居”是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给住房起的名字。夫人小张(我与邓伟志是老同学,相识相处60多年,一直称他夫人“小张”)属马,他属虎,故名。其实,“马虎居”的人一点不马虎,他们为人做事向来认认真真,兢兢业业。这归功于女主人的贤惠能干,持家有方,营造了一个民主、和睦、温馨的小家庭,“马”到功成。
女主人小张,是位十分能干、治家有方的当家人,大事不含糊,小事不马虎。披露一条“微新闻”:邓伟志是在安徽长大的,生活上大大咧咧,缺少卫生习惯,尤其不爱洗脚;可小张非常爱清洁,家里窗明几净,一尘不染,晚上洗脚是雷打不动的。“小邓,脚洗了哇?”专注于写文章的邓伟志有时随口应答:“洗了。”而小张毫不马虎,还要“查看洗脚毛巾”。几次下来,邓伟志再也不敢马虎了,养成了每天晚上洗脚的好习惯。
有情无产成眷属
邓伟志是1956年考来上海读大学的,享受全额人民助学金,是国家一手培养的,毕业后分配在华东局机关工作,住的是集体宿舍,吃的是大食堂。那时60元工资不算少,但要补贴老家的母亲和姐弟生活,就有点捉襟见肘了。他长相斯文,戴着眼镜,照片曾被虹口山阴路一家照相馆陈列在橱窗里。用现在的话说:“小帅哥,挺吸引眼球的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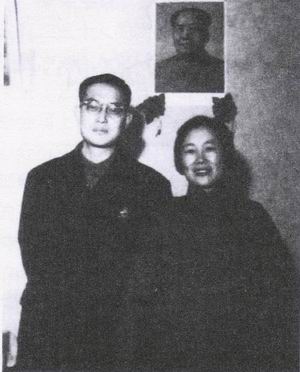
邓伟志和妻子结婚时在家中合影
同宛平路邻近的康平路弄堂里有个医务室,是为机关服务的。那里有个小姑娘,长相甜美,工作认真,口碑很好。经人介绍,他俩相识了。小姑娘姓张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,小张发现了邓不光“有文化有长相”,还有不少优点,“只要人好就好了”。1967年2月,两人登记结婚。当时双方都是无产者,婚房、大床和书桌是邓向单位租用的,想租书橱,但“级别不够”,只能借只“藤编小书架”。友人看他们太寒酸,搬来了家里的单人沙发。但他们很乐观:“面包会有的,一切都会有的”。
正是:择偶须偕千秋业,爱有源头情不竭。
主内主外一人担
邓伟志是“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”的人,被媒体称为“属书的”,“不动笔,手发痒”,平时生活越简单越好 ,“填饱肚子就行”。小张是家中长女,还有几个弟妹,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,勤劳、朴实、能干,持家有方,除了“开门七件事”,邓有时在家写文章,她还要安排午餐。最常见的是下面条,并再三叮嘱“不要忘记!”尽管如此,邓有时还是“偷工减料”。一次,他看桌上有两只馒头,就从冰箱里找点剩菜,加点酱油、麻油,倒上开水,“泡馒”吃得有滋有味,还自我解嘲:“味道比西安的‘泡馍’差一点”。午餐对付过去了,时间也省了,晚上“挨批了”。可小张是“凶”在嘴上,痛在心里:“老凑合哪能来是!”
小张持家很讲民主,女儿同样可以批评爸爸妈妈。这是家庭和谐的保证。在一次家庭民主生活会上,三人相互批评,每人先在纸片上写一个字概括另外二人的缺点,然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结果,张是“凶”,邓是“懒”,女儿是“娇”,都说到了点子上,三人都笑了,认了,并作了自我批评。此后,大为改观,家庭更和谐。
当然,和谐并非没有矛盾。邓伟志就写过一篇《我与妻子的默契与矛盾》,坦承同妻子的“三大矛盾”,张看后说:“还有一条矛盾:东西乱放。”可贵的是他们善于处理矛盾,达成默契。她家有个“三个‘三分钟’”规定,其中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“生气不超过三分钟”,并做成“黄牌”。邓有时为查找资料,“家里摊得一塌糊涂”,张不免“气不打一处来”。这时邓自知理亏,不便“狡辩”,便向她举起“黄牌”,她再看看他忙碌的样子,也就“熄火”了。有时客人来访,探讨学术问题,邓会激动地大声争论起来,女儿在家就会背着客人向爸爸举起“学会控制自己”的黄牌,邓微微点头,也就平心静气了。所以,他们家从没有什么大声争吵。
敬老爱幼皆周全
小张是2002年退休的。退休之后她反而更忙了,除了“管好”邓伟志的生活,还要照顾九十六岁高龄的母亲,母亲住在北新泾,她从市中心的家里过去路上得两个小时,尽管自己“累得要死”,但从不流露出来,陪母亲散步,帮助做些家务,还要安排弟妹轮流去陪护。弟妹对“大姐”十分敬重:“听阿姐安排”。
小张对婆婆也是敬爱有加。邓伟志这位“家中有多少钱,我不知道;每月开支多少,我从不过问”的“两不”先生,家里全由小张安排得妥妥贴贴。30年前,瞳瞳写文章收到25元稿费,母女俩一合计,给祖母、外婆、姑姑和读小学的堂弟各5元,还有5元,一家三口庆祝—下,“高兴高兴”。还有一次,女儿得了200元奖学金,给祖母100元(因为当年八十大寿)、给外婆30元,堂弟10元,皆大欢喜。
女儿九岁那年,在郑州姑姑家的祖母来信,想念孙女,希望她到姑姑家过年,但他们夫妇忙,走不开,邓提出让女儿自己乘飞机去,小张反对。怎么办?“抓阄”,结果2比1,乘飞机。瞳瞳高兴,小张也只好认账,但还有点不放心,又特地写了几封信放在女儿身边,以备万一需要时请人指路。结果,一切顺利,女儿平安到达了祖母身边,欢欢喜喜过新年。
文章的第一读者
1980年以来,邓伟志在理论界素以敢讲真话闻名,因而“得罪”了一些名人。他的文章曾引起过六场争论,有时争论很激烈,而他却“冷眼向洋看世界”,还给自己起了个“邓争议”的“雅号”。一度有人向邓“透露”:有人“盯”上你了,“可能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来批判”。邓伟志虽“心地坦然”,但也不免有不愉快的时候。每当邓情绪不大好时,小张除了安慰几句,“一句不啰嗦”,邓也“晚上睡得香,白天干得欢”。不仅如此,小张还是邓文章的“第一读者”,实际是“把把关”,看了都会“谈看法”,时常还主动借来相关资料给邓参考。邓感慨地说:“小张对我业务上的最大帮助,是最大限度地为我提供写作材料和宁静的环境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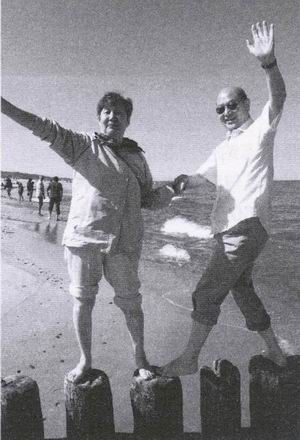
同游立陶宛
在准备出版《邓伟志全集》期间,小张同邓一起,忙忙碌碌,搜集、整理“杂乱无章”的书报刊资料,将到处乱放的文章收集起来,然后整理,分类,排序,列出目录,使邓“用起来顺手”。《邓伟志全集》排出校样后,小张又同邓一起做联络工作,送、取校样,请专家审稿,忙得不亦乐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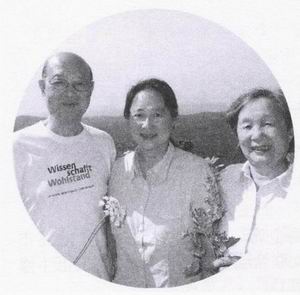
一家三口
邓伟志曾送我一册《老夫老妻》影集,是纪念他们金婚的。封面下方有首诗,是“老夫”的心声,也是对“老妻”的赞美:搀我护我五十年,再苦再累都觉甜。主内主外一人担,让我写出廿四卷。敬老爱幼皆周全,八方友人勤串连。不信长寿能挂万,只念来生仍手牵。这可以说是他们相守一生的家庭故事的最佳注脚。